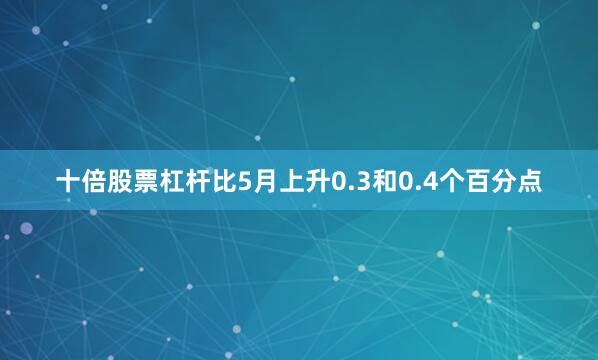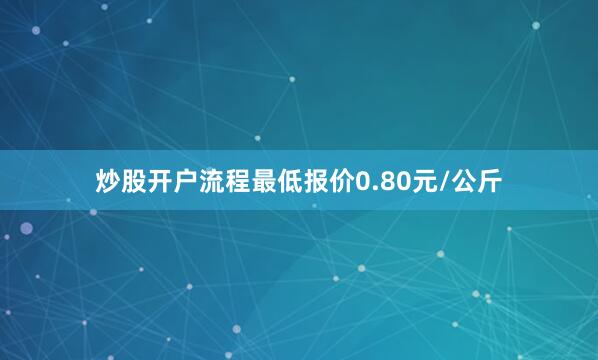作为欧洲歌剧传统的核心殿堂之一,巴伐利亚国家歌剧院在国际舞台上始终保持着顶尖水准,但气质却不同于大都会的张扬,总是带有一种独特的巴伐利亚人的谦逊与克制,同时又不失幽默。其歌剧制作以深厚的德奥传统为根基,却不满足于博物馆式的再现,观众在现场能够感受到一种难以言喻的张弛。这种既植根传统、又面向当代的双重气质,使巴伐利亚国家歌剧院的演出始终散发着一种经得起时间检验的魅力。
巴伐利亚国家歌剧院与维也纳国家歌剧院相似,采取的是“一套班底、两块牌子”的体制——演出歌剧时称为“巴伐利亚国家歌剧院”;而在举行交响音乐会时,则以“巴伐利亚国家管弦乐团”之名登场。

巴伐利亚国家歌剧院此次访华,无疑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他们为上海观众呈现的两部经典歌剧——10月1日的瓦格纳《漂泊的荷兰人》与10月2日的威尔第《奥赛罗》——均赢得了极大的成功。而在10月3日的交响音乐会中,乐团更以精湛的演绎展现了自身悠久的历史传承与深厚的艺术底蕴。

音乐会上半场演出的莫扎特的两部交响曲均完成于历史上隶属于巴伐利亚的萨尔茨堡,其中《G小调第25号交响曲》(K.183)尤为令人难忘:第一乐章汹涌的狂飙风格令人立即想到电影《莫扎特》的片头,这似乎已经是莫扎特人生之写照。这一乐章展开部开始三次模进之后出现的新主题令人窒息,之后双簧管独奏与弦乐的对话悲天悯人。第二乐章婉转低回的歌唱性与第一乐章的戏剧性形成鲜明对照。在巴伐利亚国家管弦乐团的演绎中,这种对比被塑造得格外清晰而动人:他们的音响精致、剔透,仿佛每个声部都镶嵌在晶莹的质感中;而戏剧性的转折与矛盾冲突又被拿捏得恰到好处,不流于夸饰。即便在最激烈的时刻,乐团依然保持着古典的矜持与端雅,使音乐在激情与克制之间呈现出一种罕见的平衡与高贵。那一刻,所谓“含着眼泪的微笑”便不再只是比喻,而是化为现场鲜活的体验。

《蒂尔的恶作剧》仿佛被理查·施特劳斯施下了魔法。开篇圆号演奏的蒂尔主题,始终是圆号演奏家的试金石。巴伐利亚国家管弦乐团的圆号手们亦未能完全逃脱这“魔咒”,出现了细微的偏差——正如1944年施特劳斯本人指挥维也纳爱乐的排练录像中,同样难免失准。然而瑕不掩瑜,乐曲真正的开场白来自小提琴组,他们清澈而灵动的音色令人耳目一新,这种鲜活的质感唯有在现场方能体会。指挥尤诺夫斯基别具匠心,将最强烈的高潮留在蒂尔受审之前,而在表现他对权威的蔑视时却刻意收敛——甚至一度放下指挥棒,以免乐队激情过度。理查的作品层次繁复、难以驾驭,但在这场演绎中,巴伐利亚国家管弦乐团却展现出细腻而清晰的层次感,使狂放与精致并存。

自《玫瑰骑士组曲》响起,我的临响体验便被记忆深处的克莱伯所俘获。他那份无可替代的指挥气质仿佛在乐声间浮现,使我几乎忘记了时间的流动。随后的两首加演曲目——小约翰·施特劳斯的《蝙蝠序曲》和《雷电波尔卡》——更将我的思绪引向往昔:1979年,他与巴伐利亚国家歌剧院合作的《玫瑰骑士》,以及1987年的《蝙蝠》,早已成为歌剧史上的丰碑。那是属于克莱伯与巴伐利亚国家歌剧院的黄金时刻,也是一代乐迷心中的永恒典范。今夜的演绎,让未曾亲历其现场的人们,仿佛在瞬间触及那段传奇的余晖。

余晖也在《玫瑰骑士组曲》中闪耀。这部犹如电影画面般的乐曲,给了我们如哲性人生般的情感体验。元帅夫人为了成全年轻的奥克塔维和苏菲而默默退场,这段小提琴的独奏呼应了本场音乐会中蒂尔之死,当然还有《堂吉诃德》中老骑士之死,更令人想到理查写于1948年5月6日的艺术歌曲《在晚霞中》(选自《最后的四首歌》)的唱词:“哦,多么辽阔而寂静的安宁!血红的黄昏这么深沉,我们如此厌倦流浪,这难道意味着死亡的降临?”这是理查的天鹅之歌。

老魔法师理查·施特劳斯却以圆舞曲告诉我们:人生的欢乐何其珍贵,而这种欢乐并非轻佻的喧闹,而是历经磨难与沧桑后所焕发的感恩与喜悦。金色的余晖洒落在音乐之上,也照耀着人性的欢欣。尤诺夫斯基似乎捕捉到了这种哲思背后的纵情,他让乐队尽情释放,一幅幅圆舞曲的画面随之在听众眼前次第展开。理查用圆舞曲向他的前辈、“圆舞曲之王”小约翰·施特劳斯致敬;而尤诺夫斯基与巴伐利亚国家管弦乐团,则借圆舞曲向这座历史悠久的歌剧院以及伟大的巴伐利亚音乐传统献上他们的礼赞。(作者为上海音乐学院教授)
启天配资-股票配资指南-长沙股票配资公司-如何选择证券公司提示:文章来自网络,不代表本站观点。
- 上一篇:中国期货配资公司并以第一名的成绩轻松被录取
- 下一篇: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