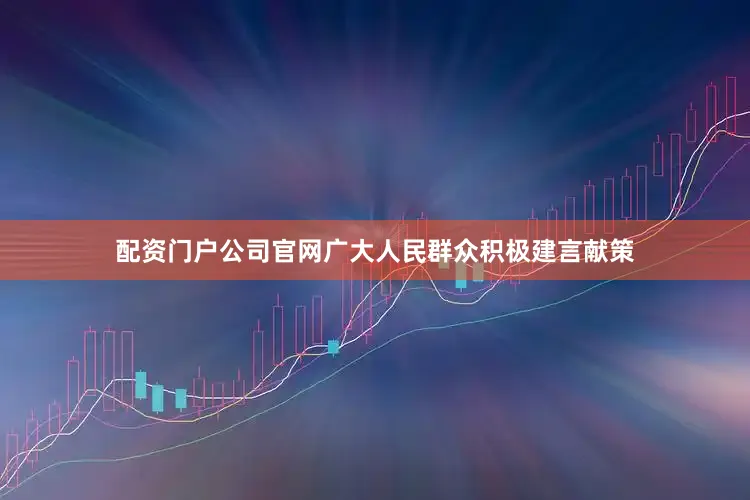清晨的雾气还没散尽时,外婆已经踩着露水从鸡窝里摸回了三个土鸡蛋。蛋壳上还沾着几撮干草,在晨光里泛着温润的粉白,像极了外婆布满皱纹的手背。她总说,要吃柴火灶焖饭,就得用这样带着 “土气” 的蛋,还有挂在灶房房梁上、熏得油亮的腊肉。
灶房是老屋最热闹的地方。泥土糊成的灶台被烟火熏得发黑,却在墙角生出几簇青苔,透着几分生机。外婆往灶膛里添了把干松针,火苗 “噼啪” 一声窜起来,舔着黝黑的锅底。她从米缸里舀出三碗珍珠米,倒入竹编的筲箕里,接着就去院角的井边打水。井绳磨得发亮,轱辘转起来发出 “吱呀” 的声响,清凉的井水带着草木的气息,漫过雪白的米粒。外婆淘米时动作很慢,手指在水里轻轻搅动,米香便随着涟漪一圈圈漾开,混着灶膛里松木燃烧的味道,在空气里酿成一种让人安心的香气。
等米泡得发胀,外婆就把它们倒进铁锅,再添上刚好没过米面的井水。她用筷子在米中间戳了几个小孔,说这样 “气才能跑通”,饭粒才会颗颗分明。盖锅盖前,她总会往锅边贴一圈玉米饼,面团是前一晚发好的,掺了切碎的南瓜丁,贴在锅壁上滋滋冒油,很快就结出金黄的锅巴。
展开剩余61%这时该轮到腊肉登场了。那腊肉挂在房梁上快半年了,表皮熏得乌黑,内里却红得透亮。外婆取下一块,用温水洗去表面的烟尘,菜刀切下去时,肥肉部分发出 “沙沙” 的轻响,瘦肉则带着韧劲,要费些力气才能切断。切好的腊肉丁肥瘦相间,在碗里堆得像座小山,油光顺着边缘往下淌,落在桌上凝成小小的油珠。
土鸡蛋要等到饭快熟时才打。外婆把鸡蛋在锅沿轻轻一磕,两手一掰,金黄的蛋液便滑进瓷碗里。她从不加味精,只撒一小撮盐,用筷子快速搅动,蛋液起泡时,碗沿会沾着细密的泡沫,像撒了层碎银。灶膛里的火渐渐小了,她往里面添了根粗柴,让余温慢慢煨着锅里的饭。
大约半个时辰后,锅盖边缘开始冒白汽,带着一股混合着米香、肉香和蛋香的热气,顶得锅盖微微颤动。外婆掀开锅盖的瞬间,一股白雾 “腾” 地涌出来,裹着滚烫的香气扑在脸上。原本平整的米面鼓起了一个个小丘,腊肉丁嵌在饭里,肥肉的油都渗进了米粒,让每一颗米都染上琥珀色。她把蛋液沿着锅边淋下去,蛋液遇到热气立刻凝固,边缘变得焦香,中间却还带着点溏心。最后撒上一把葱花,绿得发亮的碎末落在油亮的饭上,像突然绽开的春天。
我总爱在灶房里等着开饭。外婆会先铲起锅边的玉米饼,饼底的锅巴脆得能咬出声响,里面却软乎乎的,带着南瓜的甜。然后她用木勺把饭盛进粗瓷碗里,每一勺都要挖到锅底,这样才能同时吃到软糯米粒、焦香锅巴、油润腊肉和嫩滑鸡蛋。第一口下去,先是鸡蛋的鲜裹着米香在舌尖散开,接着腊肉的咸香慢慢渗出来,最后锅巴的脆劲带着微甜的余味,让人忍不住加快咀嚼的速度。
外婆坐在灶门前的小板凳上,看着我狼吞虎咽。她的眼睛眯成一条缝,眼角的皱纹里盛着笑意,像盛着阳光。“慢点吃,锅里还有呢。” 她说着,往我碗里又添了一勺,“这柴火灶焖出来的饭,就得配土鸡蛋和腊肉,不然总差着点意思。”
我后来在城里吃过很多焖饭,用电饭煲做的,用砂锅炖的,甚至加了鲍汁和海鲜,却总觉得少了点什么。直到某个冬天的傍晚,路过一家柴火灶饭馆,闻到相似的香气,才突然明白,少的是灶膛里跳动的火苗,是外婆淘米时的耐心,是腊肉在烟火里慢慢沉淀的时光,还有那土鸡蛋里藏着的、带着晨露和阳光的味道。
那味道,是外婆用一辈子的烟火气,煨出来的乡愁。
发布于:上海市启天配资-股票配资指南-长沙股票配资公司-如何选择证券公司提示:文章来自网络,不代表本站观点。